你能愉快读完 我便欢天喜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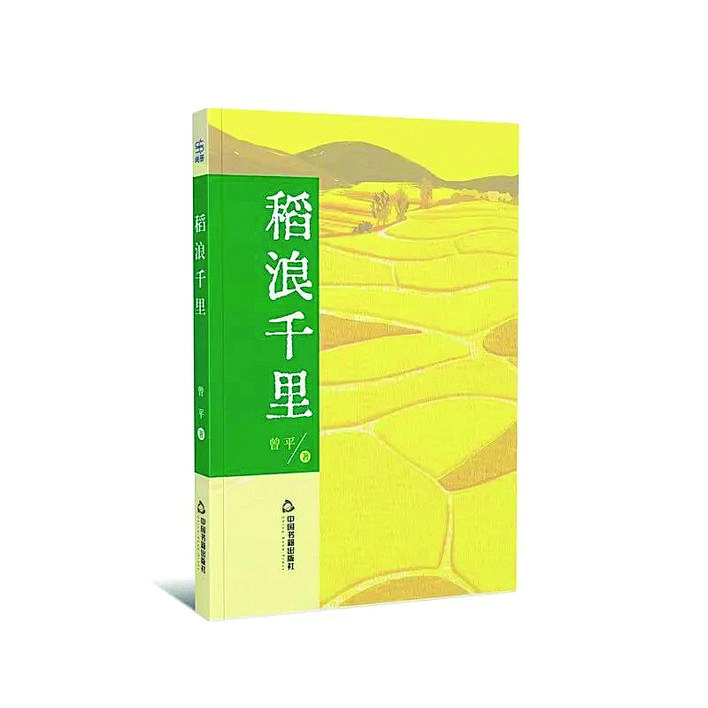
自从在高中时写些快板书、三句半、小演唱之类,从此便与“文学创作”扯上了边;高中毕业之后在小山村煤油灯下熬出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和平文艺》油印的一份小报;得到的第一份稿费,是20世纪70年代初《惠阳报》(《惠州日报》前身)寄来的两元钱。于是,苦也好,酸也罢,严冬酷暑,寒灯之下,笔耕不辍。如那旋转的陀螺,没有停下来的节奏。
希望作品有温度,让人产生共鸣
1998年,出版了第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放牧乡思》,著名作家张永枚、陈俊年为我作序,为有些怯场的我撑腰。受宠若惊之际,也迈着战栗的步子,开启了自己的文学之旅。
2013年,又出了一本《岭外春声》,斗胆请了两位身居京华的作家刘虔老师和孙立仁社长为我作序,在文学长辈的鼓励和亲友文友的吆喝声中,迈出的脚步似乎没那么胆怯了。
10年前,我忽然爱上了钢笔画,并出了一本钢笔画集《钢笔生画》。有人问“何以移情别恋”?其实,我并没有偏离重心,也可以说是“双笔齐下”。画画的笔,终日不辍;为文的笔,仍在挥写。今年夏收时节,我将过去十年的文学作品盘点了一下,似老农民将仓库里的陈年稻谷拿出来翻晒,发现好像已可以装满一个箩筐,够出一本书了。没有太多的想法,就是给自己一个交代,为一段文学路途立下路标。其实,于我而言,还有一个小夙愿,是对部分读者真情的回报。
《岭外春声》出版后,接到一位陌生读者电话,问我是否在十几年前出版过一本叫《放牧乡思》的书?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说当年曾在新华书店买过一本,看过之后却被同事顺走,他又去买了一本,又给另一个朋友拿去。几年后他在新华书店上班的家姐清理仓库时,又发现还有一本,马上买下来送给他。但书已脱页,他小心贴好,模糊的抄正,有些喜欢的文章还打在电脑上。他告诉我说喜欢得不得了,日夜吟诵阅读,很多句子都能背诵下来,还打算用英语将整本书翻译出来。深圳一位朋友告诉我,说她有个亲戚平时看书翻一二下就放下,但那天晚上看到我的书,看了两三个小时还不放手,后来干脆将书拿走了,他说他不懂农村,想看看农村人是怎么生活的。有位读者说,她将书带回家中,她父亲看到后,爱不释手,说要带回北方老家去,让亲友们分享。还有一位是全国一级战斗英雄,他很认真地看了《放牧乡思》后,嘱咐我,如出新书,首先要送他。也有人说,看我的“我娘的苦俭生活”看哭了,说边看边流泪,联想起了她的苦命妈妈。也有人说,我们看你的书,是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看写你母亲的时候是哭,但看你的“我的从厨之路”却又窃笑不止。也有许多读者看了我的第二本书后,问还有没有第一本书?
我心里比谁都明白,我的书没有那么大的魅力和功能,没有那么高的境界和理想,能让人又哭又笑,我是万万没有想到。有人看我的书我已谢天谢地,能看出眼泪和笑声,我得感谢读者。因此想到艺术的力量,也想到作家的责任,作品是有温度的,是倾注了作者感情的,如何让人产生共鸣,感情得到升华,这才是文学的本旨,也算是我的初衷。
汇编多类文章,分享阅读心得
收入《稻浪千里》这本集子中的文章,没有惊天动地之作,都是自己人生经历一些事情的回顾;有些是为参加征文的应景之作,还有幸获奖了的作品;在报社工作期间,由于工作原因,采访了二三十个文艺明星,都先后在《惠州日报》《南方日报》发表了,没有全收拾在集子中,这次选取了两位有特色的著名老艺术家专访;还有一部分是应文友之邀,为他们的新书作序,这不是我的强项,也没有太合格的资历为人作序,但人家热情相邀,也就勉为其难斗胆上阵,同时还会写下一些对作品的评论感想。写这类文章,我也不会随意应付,要通读作者的全部文章,要了解作者的人生经历,甚至还要实地采访。虽然自己的文笔不咋的,但认真还是需要的。
“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我觉得自己的人生,就在我的笔下慢慢流逝,写尽浮华,磨走岁月。我没有后悔,没有抱怨,也谈不上很大收获,更没有什么渔利,只是一种本能释放、一种自觉行为,也不敢奢望读者在看完我的书后,有什么感悟,有什么收获,你能愉快读完,我已欢天喜地。(曾平)
- 上一篇:再现雷锋从平凡走向伟大
- 下一篇:红研所校注本《红楼梦》 再出修订新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