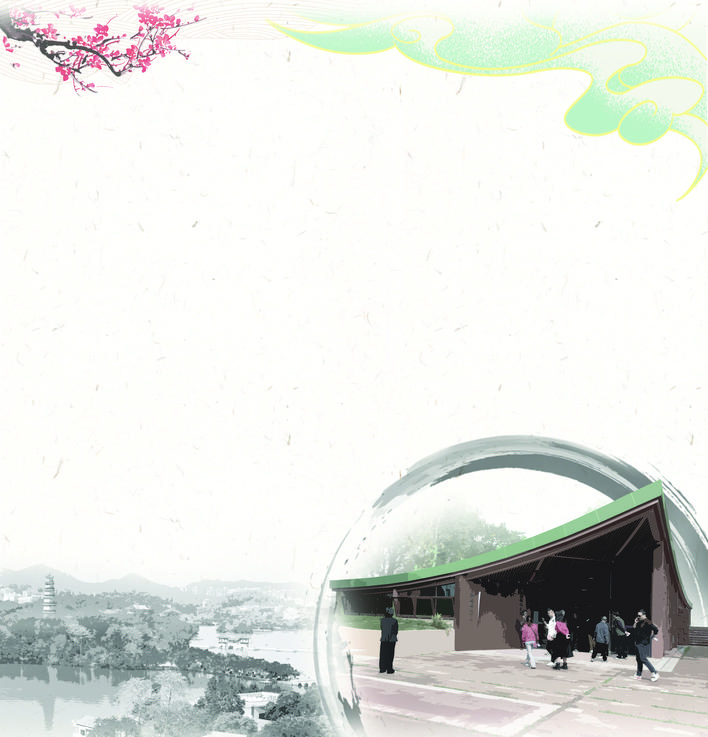
2月6日,惠州府衙遗址展示馆建成开馆。 钟畅新 摄
每座城市,都有一个原点。
这个原点纵贯古今,横联万物,神奇而恒久。千百年来,城市发生过的故事、来过的人,无论大小,都直接或间接与之相关。任沧海桑田变化,城市的原点始终如一,只要站在这里,就可以听见这座城市的脉搏生息,看见这座城市的岁月印迹,想见这座城市的文明历程。
惠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数千年的文明,沉淀在这片山海相拥的土地上,以至于今,古迹星罗棋布。龙门的庙山,博罗的横岭山,惠东的白马窑,仲恺的蚬壳角,大亚湾的针头岩,每一处都是一部充满特色的神奇大书,各自堆叠起厚厚的时光页码。而惠州的城市原点,便是府城之中的梌山。
梌山地处东江和西湖的交汇处,水运便利,山河为险,更辅以城墙,坚不可摧,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明朝嘉靖七年,一位生而颖悟、廉静善文的归善老人,宦游四方之后,放下厚厚的案牍谏章,看着侘寂的书斋,决定要为自己的家乡惠州写一本传记。惠州是他对策金殿、题名金榜、指点天下的起点,他对这里太熟悉了,可写要写的东西也实在太多了,该怎么为这本书立起纲领呢?
沉吟良久之后,他决定“致广大而尽精微”,以山河人文之最为经纬。于是他提笔写道“夫惠之山,罗浮为大;水,海为大;宫室,以公署为大”,全书以“大”为纲,这本书就唤作《惠大记》,这位老人就是明代著名的廉直御史郑维新。
书成之日,开风气之先,成为乡邦著作的标杆,后学“文献赖焉”,也是惠州现今传世最早的志书。这里的“公署为大”指的就是位于府城梌山的惠州府衙,也就是现在的惠城区桥西的中山公园,曾经的“惠州第一公园”。在古代,这里既是惠州的政治中心,也是惠州这座城市的原点,为了守护这个原点,惠州临江制湖,筑成天堑雄堡,安稳数千年,福泽百万生灵。
这里的故事要从汉武帝元鼎五年说起。这一年,南越国土人领袖、丞相吕嘉杀害了亲汉派的国主赵兴,以及终军等多位汉朝使者。这位终军就是让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在《滕王阁序》写到“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的终军。当时,英姿勃发,心雄万夫的王勃,自比于终军,依然满是艳羡仰慕,其才略可想而知。终军少年成名,很受汉武帝的器重,青年死于岭南,千百年来,他也成为文人心中扼腕叹息的大英雄,身虽死,神不灭。
赵兴、终军等人被杀,让汉武帝极为震怒,他派大将路博德、杨仆领军十万,水陆分进,攻灭南越国,使百越归制。自此由赵佗创建的南越国,历经五王,享国九十三年,终于谢幕。灭亡南越国之后,汉武帝将南越故地分设成九个郡,其中就包括隶属于交州的南海郡。南海郡下设博罗等六县,并在博罗县设“洭浦官”主管水利,统治区以粤东为主,兼及粤北局部。“博罗”与“缚娄古国”同音同根。感于其事,北宋咸平年间,陈尧佐任惠州太守,他站在梌山府衙公堂外的野吏亭,看着山下的苍茫东江,写诗赞道:“叠巘分诸粤,重城截大荒。耕桑蛮聚落,烟火汉封疆。”
自西汉元鼎六年南海郡下设博罗县,一直到梁武帝设梁化郡,期间六百余年,博罗县治一直设在古梁化,即现在的府城梌山,由于其深远的政治影响,古梁化也成为惠州全境的古名。叶梦熊之孙,雍正《归善县志》的作者叶适在追溯家族历史中也曾写道“成化元年乃迁于梁化万石方”,这里的万石方就在梌山旁,并且他自注“惠州古名梁化”。梁化郡设立之后,梌山升级成为郡治所在,博罗县治则迁于相对偏远的“东江北岸浮碇岗之西”,也就是现在的博罗县治罗阳。
隋开皇十年,隋文帝杨坚平定南陈之后,派襄阳郡公韦洸、东莱郡公王景持节巡抚岭南,百越皆服,随后在两广地区设桂州、广州和循州三个总管府,分治岭西、岭南、岭东三个地区。在隋朝,总管府是地方最高等级的行政单位,上承中央,下治军政,统御一方,其职权类似明代两京十三省中的“行省”。循州总管府的衙署就设在梌山,初期统辖循、潮二州,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仅循州一地就有编民6420户,数万人。
当时天下初定,岭南仍然不安宁,和东莱郡公王景一同来岭南的襄阳郡公韦洸,就战死在广州总管的任上。作为循州首任总管的樊子盖,他没有选择与土人激烈对抗,而是恩威并用,既廉且能,怀柔百姓,深受爱戴。《隋书·樊子盖传》记载他“爱惠为先,抚道有方,宽猛得所”。在循州总管任上十年,他营建衙署,凿井惠民,宣扬教化,促进了惠州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同时也加深了岭南与中原的联系。
开皇十八年,樊子盖进京述职,朝见隋文帝,他向隋文帝杨坚面呈了岭南地图和方物,直述循州及岭南的重要性。岭南就这样直观地展现在皇帝面前,隋文帝听后大喜,旌表樊子盖之功,大加赏赐良马杂物,并且使其“加统四州,令还任所”,循州总管府面积最大之时,大致为今河源、梅州、惠州、汕尾、汕头、潮州、东莞、深圳等市之地。
自此,粤东政令所出,皆从循州,梌山俨然成为粤东城市群落的原点所在。
十余年间,樊子盖将循州治理得井井有条,人口不断增长。他对循州感情很深,离任后他曾对隋炀帝说:“臣一居岭表,十载于兹,犬马之情,不胜恋恋。”隋炀帝深受感动,对他封赏甚厚。樊子盖的继任者、第二任循州总管柳旦,传递薪火,更是在梌山之上积极传播儒学,兴办文教。惠州,传出朗朗书声。
此后千余年里,梌山一直作为惠州府衙所在。北宋时期,当苏东坡从梌山之下的横水渡登岸之后,看见府衙官署之雄壮,草木之青葱,写下了“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的惊喜。第一站住在皇华馆内之江楼,苏东坡又写出佳句“海上葱昽气佳哉,二江合处朱楼开。蓬莱方丈应不远,肯为苏子浮江来”。第二年春夏之交,还是在梌山府衙官署,他一边食荔枝,一边写下“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成为惠州至今最广为人知的名片和标志。
洪武元年,天下大定之后,为稳定岭东,惠州设府,府衙还是设在梌山。此时的惠州府“东接长汀,北连赣岭,控潮梅之襟要,壮广南之辅扆,大海横陈,群山拥后”,是名副其实的岭东雄郡。第三年,惠州知府万迪带领百姓,以府衙梌山为中心,以东江西湖为险,在宋代故城的基础上扩建惠州府城,修筑城墙,自此,奠定了明、清两朝数百年惠州府城的规模和格局。
“铁链锁孤舟,浮鹅水面游。任凭天下乱,此地永无忧。”以梌山为中心的惠州城固若金汤,在冷兵器时代,从未被攻破。清朝初定,清政府便将广东省最高军事机构广东提督府设在梌山。第二次鸦片战争,侵略者攻陷广州,两广总督黄宗汉“以省垣不靖,驻节惠州,以控华夷”,使英法联军甚为忌惮。
民国建立后,梌山之上的惠州府衙的政治职能成为历史,但是长期的军事浸润,使得惠州人养成了崇文尚武、坚毅勇敢的精神面貌。作为海防重地,革命名城,惠州也是近代民主革命策源地之一。以廖仲恺、邓演达、叶挺为代表的“惠州三杰”登上历史舞台,推动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周恩来也曾登临梌山,发表演说,悼念阵亡将士。
随着封建时代的结束,梌山,这一惠州历史的原点,政治功能逐渐隐退,曾经传承千年的府衙也成为遗址。但是这里东临东江,西倚西湖的优美环境,依然吸引着每一个来惠州的人。此后这里被开辟成惠州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园,后又建立中山纪念堂,成为广东省四大中山公园之一,至今仍是惠州市民休闲散步的好地方。
公园的设立,避免了梌山一带在城建浪潮中的过度开发,也使得这一惠州历史的“聚宝盆”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2021年,为保护文物,配合中山公园升级改造工作,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惠州府衙遗址进行了局部挖掘,出土了惠州府衙官制建筑遗址、隋代铭文砖、“隋井”等遗迹和文物,沉寂百余年的惠州府衙,终于重光于世。
这次发掘对研究岭南地区官式建筑和惠州历史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证价值。为了“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惠州市委、市政府在这里设立惠州府衙遗址展示馆,我也有幸参与,应邀负责主笔撰写遗址的布展大纲和解说词。
走访和采写的过程中,每次站在千年古城的原点梌山,看着川流不息的东江水和西湖边的车水马龙,尘封已久的历史血脉,仿佛依然热烈地跳动着,讲述着古城的无限风华。
(曹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