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葫芦岭贝丘遗址上的贝壳积层。

博罗葫芦岭贝丘遗址公园。

在平海舂碓石遗址发现的各种石器。

石镞。

疑似古人打磨过的“砍砸器”。
石锛。
石镞。
石斧和石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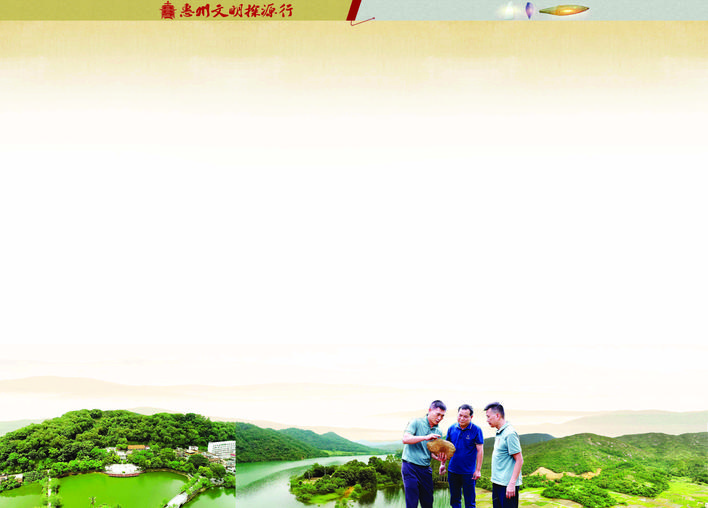
葫芦岭贝丘遗址 水东陂水库 平海舂碓石遗址 在水东陂林场发现疑似“砍砸器”的石头。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提出,中华文明的起源“不似一支蜡烛,而像满天星斗”。意思是,新石器时代直至夏商时期,中华大地同时存在着风格各异的众多文明,散布在四面八方,犹如“满天星斗”。
这满天星斗中,岭南惠州就是其中一颗,在时间的长河中闪烁。千万年间,沧海桑田,回头看,东江先民在那里奏响的,正是惠州文明的先声。
山川孕育
岭南历史始于原始社会的原始群时期
岭南,是中国南方五岭以南地区的概称。五岭由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五座山组成,大体分布在广西东部至广东东部和湖南、江西四省边界处。
惠州地处大庾岭之东,西屏省城,南卫海疆,带山襟海,形势雄壮。“惠之山,罗浮为大;水,海为大。”惠州的山川形胜,大气雄美,明嘉靖进士李义壮《重修惠州府城记》称“惠之为郡,东扼梅潮之冲,西接汀赣之胜,北负浈韶之重,南瞰渤海之险。崇山奥壑,蛋岛鲸宫,不二三百里而遥,诚雄郡也”。
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则称,惠州“东接长汀,北连赣岭,控潮梅之襟要,壮广南之辅扆,大海横陈,群山拥后”,将惠州“粤东门户”的战略地位阐述得极为精辟透彻。
游历大半个中国的苏东坡曾说,惠州“环州多白水,际海皆苍山”,形象地勾勒了惠州地理环境的基本特点。
据清光绪《惠州府志》记载,惠州境内之山脉,以东江为界分南北二条。南条宗莲花山,始于兴宁,尽于惠城区;北条宗九连山,始于和平,尽于博罗。
惠州北依九连山,南临南海,位于粤东平行岭谷的西南段,地貌类型复杂。地势北、东部高,中、西部低,中低山、丘陵、台地、平原相间,在丘陵、台地周围以及江河两岸有冲积阶地。其中,中低山约占全市陆地面积的7.7%,丘陵占26%,台地占35%,平原阶地占31.3%。
北部和东部见天堂山、罗浮山、白云嶂和莲花山等集结形成的中低山、丘陵,多为东北—西南走向,呈平行排列。市内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峰30余座,其中惠东县的莲花山海拔1336米,为市境第一高峰。中部和西部主要为东江、西枝江及支流侵蚀、堆积形成的平原、台地或谷地,在龙门县平陵、龙江、永汉及博罗县公庄一带见喀斯特岩溶地貌;南部毗邻南海,海岸线曲折多湾,全长223.6千米,属山地海岸类型,岬角、海湾相间分布,形成复杂的侵蚀—堆积基岩港湾海岸。
从地质学的角度来看,如今惠州地区的山川地貌,形成于距今200~300万年的新生代第四纪。
有山必有川。中国的地形就整体而论是西高东低,遂百川皆向东流。惠州则相反,整体地势是东北高、西南低,呈现东北往西南走向、谷峰相间的地貌格局,造就东江和西枝江水从东向西流。在道教理论看来,东往西流之水为“逆水”,是“仙源福地”。苏轼在《惠州李氏潜珍阁铭》有云:“悼此江之独西,叹妙意之不陈。”
东江被称为惠州“母亲河”,古称龙江,发源于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由赣南进入广东河源龙川境后,一路向西南奔流,经过惠州、增城、东莞,由虎门出珠江口入南海。东江全长约520千米,流域面积约3.5万平方千米。
山川之气,呼吸相通,滋养灵长。
人类出现,世界的历史才开始起笔。正如恩格斯所说:“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
根据考古发现,河北泥河湾马圈沟、陕西蓝田上陈等遗址有距今200万年左右的文化遗存,这是目前中国乃至东亚地区可以确认的年代最早的遗存。在华夏大地上,曾经生活着170万年前的云南楚雄“元谋人”、115万年前的陕西“蓝田人”、50万年前的周口店“北京人”和距今约2万至3万年的北京“山顶洞人”。
在广东,考古发现迄今为止最早的古人类文化遗存是云浮市郁南县磨刀山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距今60~80万年。广东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古人类化石是曲江马坝人,距今13万年左右,属于早期智人,还有西江流域封开县垌中岩、云浮蟠龙洞也发现年代相近的早期智人化石。
岭南地区的历史,早在原始社会的原始群时期就已经开始。从遥远的古代起,东江先民就在岭南大地上繁衍生息、劳动创造,不断改造自然和改进生活,缔造远古的文化。
知所从来,方明所去。
矗立罗浮山飞云顶之巅俯瞰大地,徜徉南海大亚湾之畔举目远眺,早期东江先民,他们生活聚集在哪里?他们创造了怎样的文化?他们是如何推动东江地区从蒙昧走向文明?
时空链条
东江流域惠州地区已发现30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
考古是破解历史密码的重要手段。根据考古发现,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先民们就已经在惠州境内的东江流域繁衍生息,创造了惠州乃至东江流域的远古文化——我们可称之为“东江人”。
早在1938年至1940年间,意大利籍天主教神父麦兆良、考古学家到粤东的惠阳、揭阳、潮安、饶平、五华、龙川、梅县、大埔等县以及福建诸县进行考古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写成《南中国的考古》论文。论文将惠州纳入“韩珠区域”,并认为原属惠州府管辖的海丰是区域内最重要的地方,有着新石器时代早期特征的“北沙坑文化”,从而推翻了当时西方认为中国南方没有新石器和青铜文化的结论。
新石器时代,是指旧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之间的一个历史阶段,以使用磨制石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中国各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不平衡,学界认为,黄河、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开始于一万多年前,至4000年前夏朝建立结束。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结束的时间晚于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或延续至商周时期。
新中国成立迄今,考古界在东江流域惠州地区先后发现30余处新石器时代的人类生活遗址,如博罗罗阳葫芦岭,石湾苏屋岗、何屋岗、黄巢墩,潼湖蚬壳角,惠城西枝江古渡头,惠东平海舂碓石,考洲洋龙舟山等地的人类生活遗址。
考古人员先后在这些遗址发现大量贝壳、陶片及远古先民使用的石器,出土的石器品种繁多,有石斧、石锛、石矛、石锄、石戈等,有力地证实早在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东江先民就在惠州及东江流域聚居劳作、繁衍生息。
如潼湖蚬壳角遗址,地处东江之畔,高于东江水面约3米,面积约3000平方米,东西长80~100米,南北宽约40米,堆积层0.4米,考古人员曾在此采集到打制石斧、石锛、磨制石斧、夹砂细绳纹陶片和夹砂陶器座等器物。其中,磨制石器主要在刃部磨光,个别为通体加磨,器身留有较明显的打琢痕迹。该遗址出土器物的特征与珠江三角洲地区目前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接近,遗址年代距今约5000年,为研究惠州市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和史前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惠州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器物,以磨光石器的数量和种类为最多,这些石器采用的石材主要是硅质石灰岩,质坚而性脆,从石质颜色、制造工艺来看,与南海、高要、阳春、东莞、增城等地发现的磨光石器类似,应属广东新石器时代“西樵山文化圈”的磨光石器,具有独特的岭南风格。
在遥远的新石器时代,惠州处于原始社会状态,没有具体名称,是一片比较平静的土地。
惠州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大量纹饰精美的陶片和工艺独特的磨光石器,表明这些遗址所在地在新石器时代中期至晚期,为东江流域先民的部落聚居地。
这些遗址在文化形态上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是珠江文化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从时空格局上看,则构成了一条大体完整的惠州史前文化发展链条。
《韩非子·五蠹》说,“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这里描述的是原始社会古人采集、渔猎的生活场景。
旧石器时代的人类住在山洞里或树上,采集植物果实、根茎,同时也集体狩猎野兽、捕捞河湖中的鱼蚌。至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人类已经学会了摩擦取火,并发明了弓箭,摆脱了茹毛饮血的生活方式,逐渐走出野蛮状态。
“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载于东汉赵晔《吴越春秋》的八字诗歌《弹歌》,被认为是上古时期的歌谣,描写古人从制作工具到进行狩猎的全过程,生动反映了原始社会的狩猎生活。
在东江两岸和南海沿岸,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特别是水产资源,为当时以采摘、狩猎、捕捞为主要生产手段的东江先民提供了较为充裕的物质条件。
进入新石器时代,从母系社会过渡到父系社会,先民以自然经济为主,原始农业和定居先后出现,且相辅相成,交替演进。
惠州新石器时代遗址山海交辉,大都近河或滨海,且以贝丘遗址为主。
考古学者莫稚的《南粤文物考古集》记载,目前惠州惠城区有2处、博罗县有9处河岸型贝丘遗址,全部分布在东江两岸。
例如博罗葫芦岭贝丘遗址,濒临东江,东西约150米,南北约50米,高约60米,从岭顶到岭脚被厚厚一层灰白色沙蚬螺蚌类贝壳所覆盖,表明了生活于此的先民部落规模颇大,并且聚居时间较长。
像这样堆积深厚的贝丘遗址,仅邻近东江的博罗石湾镇,就有苏屋岗、何屋岗、黄巢墩3处。
蚬类、蚌类的肉可食,壳可用来制作工具和装饰品,这些食物的捕捞也相对容易,是新石器时代沿海或沿河居住的先民经常食用的食物。
此外,在惠州中山公园西偏4米之下土层中,以及在东新桥东面桥头3米之下土层中,亦发现大量贝壳。
这些贝丘类型的远古人类生活遗址,印证了居住在此的东江先民,经过渔猎的漫长历史发展过程,出现了“沿水而居”的原始聚落。
在惠东平海舂碓石、考洲洋龙舟山等滨海遗址,考古人员先后采集到石器和陶片,表明先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在海边活动,望着南海万顷碧波,探寻天地奥秘,寻觅人间温饱。其开放胸襟,在大亚湾、红海湾之畔,雏形显现。
光阴似水,唯有潮起潮落不变。此时的东江先民,“处于氏族、部落社会,民族形成过程尚未开始,属诸越族的先民,可称之为先越族群或先越人。”(练铭志、马建钊、朱洪《广东民族关系史》)
新旧交替
从“食物采集者”转变为“食物生产者”
随着时间的推移,先民部落活动范围逐渐向沿河两岸、滨海地区及河谷台地拓展,在空间形态上呈现出以东江河谷为原发点向两侧扩散的发展格局,而原始农业此时也在岭南大地悄悄萌芽。
惠州市岭东文史研究所副所长何志成的《惠州历史丛谈》记载,惠州西枝江古渡头遗址出土的一批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磨光石器,有石斧、石锄、石凿、石锛、石杵、石匕首(柄)等共约30件,这些石器石质坚硬,棱角线条清晰,柄部磨制呈流线型,手握舒适自然,有相当一部分是东江先民用以垦荒耕种的生产工具。
这些工具看似平淡无奇,却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的惠州人已经从“食物采集者”转变为“食物生产者”。
随着生产工具不断进步,那时候的惠州人开始认识到,靠天靠地不再是牢靠的出路,于是将目光转向脚下的土地,从采集、渔猎转向动植物驯化、培育,以获得稳定的食物。
这标志着农业的出现,且以水稻种植为考古依据,走过一段漫长的时光。
大量考古成果证明,农业大约在距今一万年前出现,这也正是新石器时代的开端。
一万年前的华夏大地,北方谷子、黍子,南方水稻已经完成从野生植物到人工栽培作物的转化,那时正是人类文明发展第一次浪潮——农业革命的开端。随后,更多的农作物出现,推动人类步入农业社会。
中国是水稻的故乡。2004年,在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发现了距今1.4万~1.8万年的人工栽培稻,这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稻谷遗存,稻谷起源于长江中下游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共同认定的事实。
考古发现钱塘江流域为人类早期农作物驯化中心,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遗址中,稻谷、稻叶、稻壳互相形成0.2~1米厚的堆积层,表明在当时不仅稻田已有规模,稻作技术也走出原始阶段,但当时的人们并非仅以植稻为生,水稻只是食物来源之一,采集、渔猎仍然没有离开他们的生活。
水稻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完成驯化后,逐渐北上、南下,传入中国各地。
1926年,我国著名水稻专家丁颖在广州市东郊发现了野生稻,并用野生稻育成新品种,将人们的目光聚焦到岭南古稻的起源问题上。
吴建新《岭南农业史》认为,岭南稻作传播的路径为:距今4500~5000年,岭北的稻作文化传到了石峡,之后传到粤西,初步形成粤北和粤西两地的稻作分布,距今4400年传到广州地区附近,距今约4000年又传到粤东。
早在1917年,有学者在惠州罗浮山麓至石龙一带发现野生稻。1980年,水稻专家又在惠城区古塘坳、梅湖、汝湖、三栋、河南岸、小金口等地陆续发现野生稻资源,其中以小金口白石村的野生稻为最多,面积最大。近年,有关部门在东江上游的龙川紫市坪岭头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大约4000年前人工栽培水稻的碳化稻粒,研究结果表明:其栽培稻已经较大程度地脱离了野生稻的性状特征。这一发现,弥补了粤东地区史前栽培稻考古的空白。
水稻喜温、喜湿,最适宜亚热带湿热环境,岭南常年高温湿润的环境,无疑是栽培稻谷的绝佳之地。
有了原始的稻耕农业,生产的粮食比较充裕,东江先民过着果侑赢蛤、饭稻羹鱼的生活,并逐渐具备长期定居、饲养家畜的条件。
考古人员在博罗龙溪银岗的春秋战国龙窑窑址中发现岭南最早的建筑材料方格纹板瓦、筒瓦、瓦当等,这都说明先民们在当时已掌握建房技术并能够烧制建房材料,可以建造简易的亭棚来遮风避雨和储存物品。
随着农业的出现,人们过上较稳定的定居生活,对煮熟和储存食物的用具也有了强烈需求,陶器应运而生。在惠州博物馆内,能看到一些陶器、碗、罐等生活用品碎片,和其他收藏品比起来,它们显得粗糙、朴实。但它们所代表的是东江先民最早利用化学反应改变天然物质的开端。每件新事物的产生都有它的必要条件,如果说火的使用让人类开始了食用熟食的生活,那么陶器的诞生,则彻底改革了食物的烹饪方式和存储方式。
随着生产工具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东江先民开始饲养家畜。东莞龙江、香港深湾、增城仙村和新塘、博罗铁场以及惠州西枝江古渡头等遗址发现有猪、狗、牛的骨骼和牙齿,博罗园洲梅花墩春秋窑址出土了30多件动物陶塑,都说明广东珠三角洲地区在距今4000年前后已饲养了猪、狗和牛。
这时,家庭纺织也开始出现。近年考古发掘的龙川坪岭头、荷树排,龙门江厦村庙山等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皆出土了数量不等的陶纺轮。陶纺轮是古代纺织生产中的纺纱工具。这表明,惠州地区最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掌握纺织技术。
不过,5000年前的岭南地区,气候炎热,山林遍布,河汊纵横,瘴气横生,凶禽猛兽出没。据考古发现和古籍记载,惠州一带曾经是野象出没的地方。1978年,在东江支流公庄河畔的平陵尖石角山发现约20万年前的象牙化石,送至广东省博物馆研究保存。
唐代刘恂《岭表录异》记载“广之属郡潮、循州,多野象”,宋代唐庚写《射象记》,记录了从遥远的古代到唐宋,在惠州有野象出没,从侧面印证了古代岭南环境的蛮荒状态。
当时惠州人的生活状态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当时的自然环境中,捕捞种植皆不易。东江先民耕山耘海,拥抱风浪,与大自然一再交手又彼此造就,从渔猎走向农耕,形成不同的自然经济形态。
极目不见古人,抬头却是同一片星空。当东江先民最终走出山洞,走出大山,开始建造房屋、培育谷物、饲养家畜、烧陶纺织时,他们也许没有意识到,这是伟大的壮举。
考古学家这样评价他们:从此人类由单纯地依赖自然转为有意识地改造自然,人类从攫取经济发展到生产经济,开始了新石器时代革命。
文明萌芽
由渔猎到农耕,文明因素愈发明显
如果说碳化的谷物,是先民物质生活的象征,那充满原始艺术气息的陶瓷、石器及特殊的葬礼,则是东江先民的精神写照。
当人类不再仅仅依赖大自然,食物的来源变得稳定,逐渐进化的生产工具让生活得到进一步改善,偶有吃饱喝足的时候,原始的工艺美术悄然发展。
何志成近年研究惠州西枝江古渡头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石器,发现其中有一件石锛双面分别刻有山鸡、鲤鱼图案,笔法朴拙,线条粗犷,隐含着先民图腾崇拜的神秘意义,也透露出一种原始的艺术趣味和审美意识。
另外,惠州新石器时代遗址均出土大量陶片,有方格纹、叶脉纹、曲尺纹等图案,散发着几何美术的魅力。
仔细研究这些石器和古陶器上的纹路和装饰会发现,东江先民将劳动实践和生活中的元素,或抽象或具体地反映了出来,是他们在大自然中观察和体验所得,体现出他们在工艺美术方面的高度创造力和智慧。
人类对艺术的追求是与生俱来的,这样的追求当然不止于工艺美术。惠州人爱歌,由古及今。东江先民在东江大地聚居,或穴居或半地穴居,愉快地繁衍生息,享受劳动的收获。劳作之余,手里挥舞动物尾巴或植物枝叶,按节拍踏着脚步,载歌载舞,就像《吕氏春秋·古乐》描述的原始时代人民的生活情景:“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
从考古资料看,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已经有了审美观念,如在北京房山周口店山顶洞出土了用穿孔兽牙组成的项链。东江先民也一样,就地取材,用贝壳等美好的东西装扮自己,让自己身心愉快的同时也取悦异性,原始民俗和宗教信仰随之诞生。
有了艺术创作也就有了精神崇拜,原始教育于是应运而生。东江先民出于生存和生活的实际需要,必须学习和传授各种生活劳动技能,依靠群体力量抵御和克服自然界和凶禽猛兽的威胁,原始教育因此产生。
徐志达、吴定球、何志成合著的《惠州文化教育源流》描述,当时还没有文字符号,他们结绳而治,部落的年长者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以及实际行动的示范,将在长期生产劳动中所积累的生存技能和劳动经验传授给年幼者,包括取火技术,石器、骨器、陶器等劳动生活用具的制作和使用方法,以及狩猎、采集、造房、纺织、酿酒、治病的本领等等。当然,年长者还要向年幼者传授如何进行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等宗教活动知识,让他们学会和遵守部落族群的行为准则、礼仪习俗,参加集体的宗教民俗活动等等。
该书进一步指出,这些都是原始教育的方式和内容,它既包含为了获取生活资料而进行的“实用教育”,同时也包含为了慰藉精神而进行的“宗教教育”。产生于劳动和宗教活动的歌谣、谚语、神话、游戏、冠礼、图画等等,也都是原始教育的重要手段。
在原始森林广布的史前时代,原始社会人口素质低下,直至汉唐至宋元时代,文献上还多有关于岭南瘴疠而使人短寿和多病的记载。
仲恺潼湖的蚬壳角遗址,遗存着特殊的屈肢葬习俗,反映了东江先民对生命的态度。从石器时代人类社会出现墓葬开始,其葬式就是屈肢葬。因为原始人大多数时候都是蹲坐姿势,死亡之后也是蜷缩一团,所以在当时人类的脑海中,屈肢是十分常见的姿势。随着人类的进化,文明开始产生,人们吃饭、睡觉都开始讲究起来,直肢葬才出现。
路漫漫其修远兮。就像钱塘江流域河姆渡先民一样,新石器时代东江先民兼顾采集、渔猎和耕种、畜牧新旧两种生活生产方式,是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
2006年,在惠阳镇隆窝尾坳遗址发现一处总面积约3500平方米的远古人类生活遗址,出土文物有圆足盘、罐、釜等陶器;石器则有石锛、石斧、石戈、石环等。石器制造精美,陶器纹饰的式样丰富,经广东考古专家确认,这是一处商代前期的遗址。
史学界一般以中原地区夏王朝的建立,作为中国历史上新石器时代大体结束的标志,此时在边疆地区仍保持着新石器时代的一切最重要的社会特征。当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结束,进入青铜铸就的夏、商文明时代时,岭南地区或还处于新石器时代的尾声、从原始社会转向文明社会的阶段。商朝文明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和夏朝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惠阳镇隆窝尾坳遗址的发现,填补了惠州商代遗址的空白,还为东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的完美谢幕增添了力证。
围绕着“衣食住行”和走向更远的地方,东江先民蹒跚探索,旧的技术尚未消失,新的技术便已传播开来,而每一次演进都伴随着人类智慧的提升。至新石器时代晚期,东江流域生产力不断提高,社会组织不断完善,东江先民从漂泊流徙的渔猎生活逐步过渡到聚族定居、男耕女织的农耕时代,文明的因素愈发明显。
文明滋润了历史,点亮人类前行路径。此后,东江先民继续聚族而居,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依靠集体的力量共同劳作和创造,最终完成了走向文明的突破,形成先秦时期的部落小国——缚娄古国。
这个古国的文明成果是惠州重要的历史遗产,也是建构惠州精神的重要文化基因,成为东江文明的厚重底色。
岁月轮转,时代更迭,回眸历史可以发现,东江文明表征岭南文明的独特性与多样性,构成了中华文明起源最南端的一块拼图。
今天的惠州人应该感谢那些东江先民,感谢他们创造了东江文明,为岭南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奏响了惠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