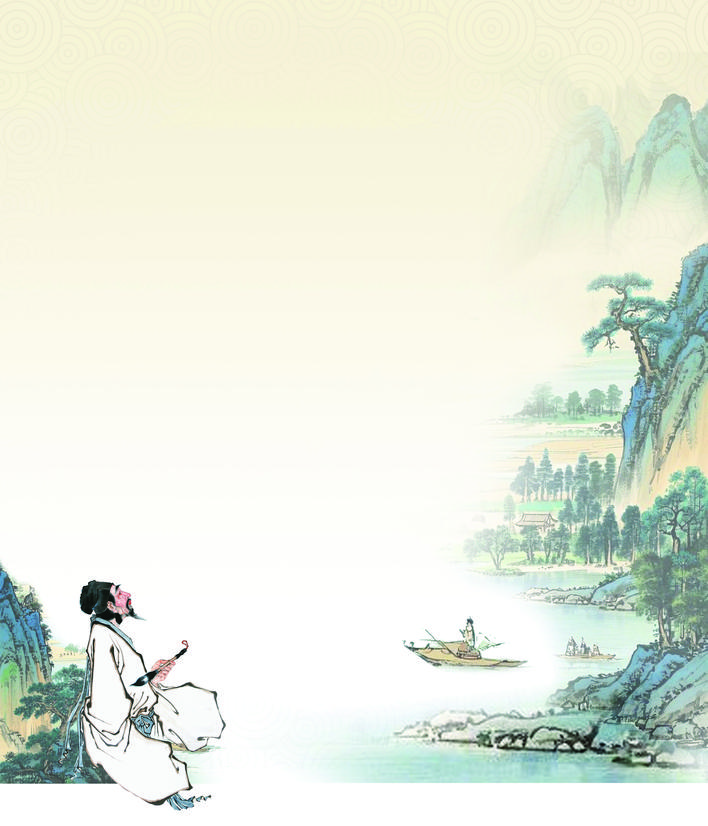
□吴定球
“环州多白水,际海皆苍山。以彼无尽景,寓我有限年”,这是东坡寓惠半年后写的诗句。将余年寄寓于此邦,当然并非东坡本意,但他对惠州“白水苍山”的无尽景色印象极佳,则是确实的,是屡屡见之于他的寓惠诗文的。例如,他诗赠僧人昙秀,就曾不无自豪地说:“人间胜绝略已遍,匡庐南岭并西湖”,把岭南秀色(当然也包括惠州山水)与著名的匡庐、杭湖风景并列而标举为“人间绝胜”。他又写信给友人刘宜翁,盛邀其来游惠州,说:“峤南山水奇绝,多异人神药,先生不畏岚瘴,可复谈笑一游,则小人当奉杖屦以从矣。”什么叫“奇绝”?奇,就是有异于一般;绝,就是达到了极致。可见,东坡对惠州山水的评价确实很高。
那么,在东坡看来,惠州山水的特点又是什么呢?他写信给曹子方说:“惠州风土差善,山水秀邃”,用“秀邃”二字来概括惠州山水的特点和优点。东坡对山川之美,历来有感悟真相的超常能力,一方山水一经他的品题,往往遂成定论,千古不易,他评说惠州“山水秀邃”也不例外。后人如宋代的杨万里以“清煞”点评惠州西湖,清代的戴熙比较杭、惠二湖特点之后,以为惠湖“以曲折胜”。其实,若是不“秀”,何来“清煞”?而“曲折”也正缘于“深邃”,杨、戴二人的品题终究未出“秀邃”二字所涵盖的境界。
东坡向中原友人推介惠州山水,往往使用类比的方法以方便对方理解。例如,他作诗示杭州西湖诸友,便说“惠州近城数小山类蜀道”;写信向陈季常形容汤泉瀑布的雄壮气势,则说:“悬瀑数仞,雷辊电散,莫可名状,大略如三军项羽破章邯时也。”向张文潜介绍合江楼的周遭风光,便说“下临二江,有楼,刘梦得《楚望赋》句句是也”;与客人在中秋月夜游丰湖,作《江月五首》记惠州湖山之美,便说“一更山吐月,玉塔卧微澜。正似西湖上,涌金门外看”,称赞惠州丰湖的玉塔微澜,与杭州西湖涌金门外的月夜美景相仿佛。写信告知陈师锡在白鹤峰买地建房,又说“新居在一峰上,父老云:古白鹤观基也。下临大江,见数百里间。柳子厚云:‘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丘也欤?’只此便是东坡新文也”;还说白鹤峰上,“江山之观,杭、越胜处,但莫作万里外意,则真是,非独似也。”这也说明,东坡常把眼前惠州的山水与著名的吴浙山水相比较,认为彼此颇相类似。随伴东坡寓惠的苏过作诗写白鹤峰新居,也说:“勿云瘴海恶,山水侣吴浙。我有环堵居,危台俯清绝”。
这“清绝”一语,既可实指在白鹤峰俯瞰到的江水澄澈至极,亦不妨理解为在白鹤峰所眺望到的数百里江山清秀至极。惠州山水的清奇绝俗,与杭越一带相仿佛,可以说是东坡父子二人的共识。
东坡对惠州山水的描写也很有特色,他有一首记游汤泉的诗叫《白水山佛迹岩》,就深受历代诗评家的赞赏,可称为东坡寓惠山水诗的代表作:
何人守蓬莱,夜半失左股。浮山若鹏蹲,忽展垂天羽。根株互连络,崖峤争吞吐。神工自炉鞲,融液相缀补。至今余隙罅,流出千斛乳。方其欲合时,天匠麾月斧。帝觞分余沥,山骨醉后土。峰峦尚开阖,涧谷犹呼舞。海风吹未凝,古佛来布武。当时汪罔氏,投足不盖拇。青莲虽不见,千古落花雨。双溪汇九折,万马腾一鼓。奔雷溅玉雪,潭洞开水府。潜鳞有饥蛟,掉尾取渴虎。我来方醉后,濯足聊戏侮。回风卷飞雹,掠面过强弩。山灵莫恶剧,微命安足赌。此山吾欲老,慎勿厌求取。溪流变春酒,与我相宾主。当连青竹竿,下灌黄精圃。
东坡以贬官身份初抵惠州,来游汤泉,面对这僻处海隅的南峤奇观,联想到这里流传着的“浮山傅罗”“古佛留踪”“饥蛟食虎”等许多动人的神话传说,不禁浮想联翩,“奇情异采,一气喷薄而出”。尤其是前八句,以雄豪笔力开拓罗浮数百里神奇境界,“云烟离合,不可端倪”。有论者以为:东坡描写岭南山水,善于捕捉其独特的形态个性,把握它的精神风致并着力描绘,“扬其异而表其奇,略其同而取其独,造其奥以泄其秘,务期天巧地灵,借人工人籁而毕传其妙。”苏轼岭南山水诗的这一艺术特点,在这首诗中得到充分展露。清人汪师韩点评此诗说:“罗浮以风雨为合离,匪此神笔,莫传其妙”。从宋代的唐庚到清代的赵翼,评论苏轼诗“叙事言简而意尽”,也都一致标举此诗“潜鳞有饥蛟,掉尾取渴虎”二句,以为其“言渴则知虎以饮水而召灾,言饥则蛟食其肉矣”;“研炼之极,而人不觉其炼者。”惠州汤泉在宋代因此而名传海内外。又如,东坡游罗浮饮卓锡泉,乘兴作一短文记之:
予顷自汴入淮,泛江溯峡归蜀。饮江淮水盖弥年,既至,觉井水腥涩,百余日然后安之。以此知江水之甘于井也审矣。今来岭外,自杨子始饮江水,及至南康,江益清驶,水益甘,则又知南江贤于北江也。近度岭入清远峡,水色如碧玉,味益胜。今游罗浮,酌泰禅师锡杖泉,则清远峡水又在其下矣。岭外唯惠人喜斗茶,此水不虚出也。
通篇未对泉水作任何直接具体的描述,而是将自己此前饮水的经历和体验娓娓道来,作层层比较,以为江水胜于井水,南江贤于北江,岭外清远峡水则又更好。“今游罗浮,酌泰禅师锡杖泉,则清远峡水又在其下矣”,卓锡泉水之清冽甘美,“甲于峤南”,不言自明。文章俯仰今昔,纵横南北,一气流转,摇曳生姿,曲尽品水理趣,仅用138字,不可谓不奇。末尾忽以“岭外唯惠人喜斗茶,此水不虚出也”一句作结,有未尽之意见于言外,更是神来之笔。宋元人有论:“子美夔州后诗,东坡岭外文,老笔愈胜少作,而中年亦未若晚年”。读此文,可知其言不谬。也可见东坡对惠州山水感情之真,感悟之深。
当然,惠州也有使东坡感到美中不足之处。他告诉友人:惠州“风土不甚恶,亦有佳山水,而无佳寺院、无士人、无医药”。在古代,士人一般指读书人;至于寺院,历来就不是单纯的宗教场所,它每每发挥着聚集、保存、展示和流播所在地方历史文化的社会功能。寺院和士人数量的多寡和素质的高低,是衡量当地人文教化深浅厚薄的重要指标。东坡每至一地,必游访名寺古刹,与僧人谈禅论道。在惠州,他就先后游访过罗浮的宝积寺、冲虚观,水北的大云寺,博罗的香积寺,汤泉的佛迹寺,西湖的栖禅寺、永福寺、天庆观(今元妙观)、逍遥堂、罗浮道院等,这些寺观大都颇为简陋,方丈道长亦鲜见大德高僧,与人文鼎盛的江浙一带相比有较大差距。让东坡看到惠州因为经济的相对落后和教育卫生的欠发达,缺少深厚的文化积累和优良的人文传统,清纯秀美的自然风光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一种原生态,需要注入缭绕的诗情和蕴藉的文气,方能韵味悠长,让人流连忘返。
也许是上苍对惠州的眷顾,恰好是东坡的到来,以其卓绝的文化魅力,为惠州山水的人文欠缺补上浓重多彩的一笔。清人沈德潜说:“江山与诗人相为对待者也。江山不遇诗人,则巉岩渊沦,天地纵与以壮观,终莫能昭著于天下古今之心目。诗人不遇江山,虽有灵秀之心,俊伟之笔,而孑然独处,寂无见闻,何由激发心胸,一吐其堆阜灏瀚之气?惟两相待,两相遇,斯人之心奇际乎宇内之奇,而文辞之奇得以流传于简墨。”
惠州的秀邃山水和东坡的绝世才情,正是这样一种积极的互动关系。东坡慧眼独具,在与惠州山水朝夕相对中,发现了它独特的天然美,激发出巨大的创作热情,借着对它的吟咏而“一吐其堆阜灏瀚之气”,形成了他人生最后的一个创作高峰。
东坡寓惠940天,写下诗、词、文、信、书画等近600首(篇、幅),除惠州西湖外,东新桥、西新桥、合江楼、嘉祐寺、松风亭、江郊钓矶、水北荔圃和大云寺、白鹤峰故居、潜珍阁、罗浮山、白水山、汤泉、九龙潭瀑布等等,凡此杖履所及,大都有作品留存,惠州山水因此而“昭著于天下古今之心目”,知名度迅速提升。仅以西湖为例,在张友仁《惠州西湖志》所收录的1400多首诗词文信(东坡作品除外),题材内容涉及苏轼事迹的占了三分之一左右,足见九百年来,东坡一直是西湖最为耀眼的人文亮点。江逢辰说:“惠州西湖处南海极滨,自鸿蒙判别,怀丽毓秀,负奇閟特,如高贤逸士潜踪晦迹,遁世无问,而沦于榛狉,盖既千亿年矣。一旦使其名赫然播四方,与夫名山大川相颉颃,而动天下后人之流慕,则自有宋苏文忠公始”,又说“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他正是从精神文化的层面上着眼,高度评价了东坡对惠州发展的历史作用。